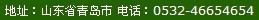|
后视镜 镜中的水渍有一个漂染的梦, 那是语言的现实未曾到达的飞地。 虚像中的风物在渐次坍塌, 因移动而产生而收容的面孔在变形。 它从不急于揭晓前方的答案, 直到前方成为下一秒的后方。 可这已是弯曲的谜底, 无法擦拭尚未结痂的路面。 如果打碎这玻璃工厂输出的弧度, 世间也许会迎来重新捏合的时刻。 沙漏里的沙子回归地面, 时间被囚禁在微小的容器。 我也许会成为无数的你, 在魔毯上飞翔的精灵停下了脚步。 静止于笔直和弯曲的博弈中, 你会重新寻找滑轮的第一定律。 同室 诗歌、同性、睡眠……多年来, 这些共需让陌生人共居一室。 最终,让你熟知的并非语言的瓣膜, 而是隐藏于后鼻音中的鼾声。 我们还没有到操戈的地步, 陌生感种植在尊重的泥土之中。 它是一夜发出的豆芽, 无需捣碎它去追逐新的菜品。 那酒意中的夜晚已无限地远去, 像褪去胞衣的麋鹿奔跑在时间的原野。 那围捕的嘴唇已遭遇口腔溃疡, 生活糜烂的部分开始新的占领。 高蹈的诗歌言论在自我清洗, 在黑暗中经历着弥留时刻。 他们从不会去祭奠这些夜晚, 任凭它们成为被海沟吞噬的火山灰。 这等同于鲸落恢宏的景象。 当它们倒塌于淤泥的宫殿。 应该有一种声呐系统可以锁定, 这曾存在于夜晚的语言仍残留着自证。 被囚的弹珠 在我祖居中的弹珠, 被封存在童年的晶莹中。 它们在可乐瓶中享受着完整, 却要不断沉湎于黑暗中的曼舞。 它们也许会怀念那破碎的同伴, 在早期流水线灯光低矮的射线中, 那彩色的颗粒成为了心脏。 哦,拣选时刻在傍晚结束! 在一个个被阳光修剪的午后, 稚嫩的手在圆润的密林穿行。 它们选择做一个个玻璃有心人, 伴随着真实世界将要吐露的獠牙。 这样的障眼法无需太久, 只需要等到疲倦时刻的盛开。 它将被收束于瓶中术的封条之中, 和蛛网成为共同沉默的邻居。 等待着终于有人褪下生活的彩带, 认定自我是黑白故事的底片。 那营救,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刻, 你应该偷偷地告诉自己: 考古学不仅仅是挖掘古墓中的棺椁, 也应该释放那被囚禁的童年。 这样,你会迎来自我的盛世, 做一个从不亏欠赤子的歌咏者。 迷路的我 十年究竟教会了我什么? 我还没有从小区学院中毕业。 面对路人的询问, (这是一场中期答辩) 我仍无法辨认那些分叉路, 给他们留下冰冷的刻板印象。 这多么像我早年去大城市得到的答案, 或许他们中也潜伏着这样的个体。 十年来,我之享受这里的地势、水文和天气, 在它的风物志中窃取着诗句。 或许,这也是一种忍受, 像怨偶之间难舍难分的情节。 我多么想投入烟尘的烽火中, 变成一朵绽放的细灰, 落入地表不断的自我修复中, 变成他叙事中转折的部分。 房子和树 从前的树掩映在房子中间, 偶尔有枝桠伸出围墙。 人的穴居是园林里的穿行术, 枝桠过剩的欲望伸进了门窗。 花萼的残片是春天散佚的书卷, 向屋里的人展示结果的决心。 就算是穷苦人家的门廊, 也会被它托举着走向仲夏夜之梦。 现在,就算移植亚马逊流域的气候, 房屋仍高耸着上帝视角的令牌。 它张开着自己笔直的伦理, 俯视着乔木弯曲的躯干。 我们甚至不知那旧居的舒展, 紧绷成为了不变的定律。 灯光烘培中的树叶无法尖叫, 它不是策兰曾注视过的桑叶。 无人再愿意为它标记学名, 在命名学中含混地涂鸦着自己。 当屋顶的棱角露出室内的虬枝, 它是对原初愿望深重的祭奠。 相依为命 被拔出地面后, 途径一场暴雨的饕餮。 杂草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像抱紧死神的豁免券。 多么甜美的晚餐: 死去同胞粘连的那点泥土, 和他们发黑的的身体。 在雨水的圆舞曲中, 这相依为命的故事终结了。 抠掉它天真的影像, 就变成死神的帮凶。 这让人想起战争的废墟, 埋藏于成片倒下的肉盾, 背后的人获得了往后的人生。 在面对祝福的时刻, 他们会在晚祷中加入这场景么? “我们本来自于尘土之中, 无非是那上帝之手的捏合, 这临时起意的偶作, 也许早就剔除了善恶的陈腐。” 语言的死皮 在其它的声音中, 我获得了某种明示, 它让我摩擦语言的死皮。 它让我长出牛背鹭之喙, 啄食饱餐后的牛氓, 那青草的碳素回到了天空。 碳基的魔力和声音在碰撞, 磷火在白骨中缓慢穿行, 生死的偈语封存于记忆的染色体。 爬行的语言,被肢解的语言, 在风中被燃烧的词根, 在氧元素的故土流浪。 当我看到那死皮中的炭疽, 那寄生的叶片舍弃了忘川, 影像复活的片段在菌丝中抽搐。 天台种植学 大型农场发出统一的指令, 占据着餐桌版图的每个兵营。 在食道年久失修的修道院, 在食谱纷繁的线粒体之中, 从不收留反对流浪的声音。 假如你拥有一片乡下的山地, 可你却不会拥有分身术的秘笈。 你无法返回那雨水的布道场, 像杜康一样酿造果肉自然的芬芳, 将斜坡也变成流奶与蜜之地。 可如果你有不曾废弃的天台, 你就应该学会俯身的哲学。 这个在油画中被重复的动作, 应变成你生活的密码, 去打开保险柜中隐藏的种植学。 这会让你食谱帝国变成联邦制, 就算收割的是海外领地的食品了, 这些也食品兑现着汗珠的附加值。 这身体中流失的琥珀在清晨发亮, 让你的肠胃回归到劳作的自我增殖。 甚至你的盲肠也在黑暗中抽动, 粗粮引领着它共振的频率。 当你重返乡间为你留存的土地, 不需要按下布满灰尘的重启键, 就能迅速分拣出神的颜色各异的种子。 雄穗和蜜蜂 暴雨重击着玉米的雄穗, 这直立的响尾蛇之尾。 夤夜后它化为细小的箭靶, 蜜蜂在雨中用嘴唇清点箭簇。 这廊柱式的图腾在雨水中发亮, 金黄的色泽噙住一个消退的隐喻。 我曾在矮凳中守护它的黄昏, 海风的翅膀曾带来理性的声响。 现在,果实正构建自我的镜像, 在盆栽的空间诗学中艰难游走。 禁欲期在潮湿中走向终结, 连接着这座城市看不见的蜂巢。 它正在甜蜜事业的顶点, 在南方濡湿的气象景观之中。 曾徜徉于荔枝和芒果的花海之中, 仍不忘贫瘠年代的玉米地。 那是无数祖先的蜂拥之所, 雄穗的图腾曾播放着基因的音乐。 天空的石灰池在夏季皲裂, 蜜蜂在叶片上吸取仅存的露珠。 天生的警觉 这些虚构的故事一直在涨潮, 淹没我用侥幸搭建的堤坝。 寄居蟹在滩涂上倔强地冒泡, 它的嘴唇是否含着海底的谶语? 你可能会想起巴菲特的名言, 看到潮水退去后的裸泳者。 天下之事充满着变数, 作为无辜的隐藏者它有过天真时刻。 这次到达应是送来一封《报任安书》, 诉说它的腮腺中被充溢的委屈。 对于这些深处的悲哀我充满警觉, 从没有用偏听让它们从耳缝中溜走。 当海鸥的汽笛喧响在红树林的矩阵, 我再一次抱紧了海浪的警戒线。 猫语者 她在天台上收拾猫笼, 为了释放它被关押的叫春声。 作为分摊者我们承受, 附带着呓语的旌旗, 让我们在它下面承受阴影。 她奇怪的语言在播散, 是气味因子在寻找宿主。 作为听觉的荼毒者, 猫的发情期是一段枯枝, 寄养着无数鲜艳的蘑菇。 如果这是声音收藏器的功效, 邻居一定动用公约来销毁。 当有人回头看月亮吞噬猫眼, 这寒光足以让声音消退。 当每个人都出让部分睡眠, 猫语在夜里变成一朵昙花, 在等待着掉落的伟大时刻。 我们无法探听那真诚的部分, 最终只能回到白昼的陆地, 猫步正捕捉着我们的眼睛, 原谅它:让视觉再次成为感官之王。 父亲的啤酒之夏 到了夏天,他就开始亲近啤酒 去冲淡埋藏于肚腩的火球。 拔罐的红在赤膊后凸现, 缓慢倾诉着中暑的掌故。 在娱乐贫瘠的面容中, 饮酒是唯一的自我游戏。 农人的一世都浸泡在酒中, 连死亡都忘记着悼词和墓志铭。 比如他上香时必须配酒, 千百年来祖先也不外如是。 神龛上永远供奉着黄酒, 也许地下需要它捂热的触须。 可我已脱离这样的程序, 重新设定城市应有的情趣。 我已很少让自己微醺, 哪怕是为了磨砺生锈的笔锋。 除非事件的风暴来袭, 露出生活塌陷的山谷。 夏季的啤酒花就会降临, 落入酒吧小小的胸腔。 扑克牌 从前,我们为生活设定底牌, 很多人丧失了勇于揭开秘密的勇气。 他们设定了失败者的角色, 在中途已走失在歧路的分岔口。 规则的制定者站在苍穹中俯视, 祂是半个梵天和半个上帝。 精彩也就那一刻被预留了, 我们永远不知道祂的脾气。 祂究竟是拯救者, 还是在嗜睡中让我们苟活。 如果让它缩小到美国剧集, 这是一场阴谋的暴风眼。 活在凯文史派西的表情里, 让无花果绽开无数个的比喻。 如果让它变成追杀令, 那五十四个逃犯将躲在哪个山洞。 大小王还能指挥卡宾枪的扳机么? 狙击手埋伏在对准洞门的风口。 有一只秃鹫开始闻到血腥, 牌面上脱落的红色引领着它。 这些引申义是童年的衍生品。 当我们将这作为游戏的开端, 我们将自己作为代码植入进去, 直到角色变成青筋, 爬满我们手臂的每一个角落, 那伴生的欲望让你无处可逃。 受困 她受困于一本命书, 在自然中脱落的松果, 被她解读成命运的敲打。 但额外的意义无处不在, 比如牛顿和苹果的轶事。 那金丝珐琅的镶嵌如此完美, 让你找不出零星的破绽。 她望着神龛的最高处, 北极光一般的烛火在闪耀。 蒲团变成天启般的释迦果, 幻化出莲花的纹路。 道路开始遮蔽脚印的渊薮, 雨滴催生出嫩芽的戒条。 在形而上的家园里, 你的莲心不容半颗反叛的水滴。 就算沙漠的隐喻随之奔袭, 你依然享受这样的旷野。 在热浪中自我渡厄, 你是众生中最先开始的个体。 你设置这样的难题, 只为自我开辟死结中的活结。 你无意于它的探索意义, 你是骑鲸而去的素人。 请叫我让·皮埃尔伯爵 从某一天开始, 他摒弃了英文系的桂冠, 甚至包括伦敦腔的宝石。 他穿着从南浔买来的真丝睡衣, 想象着他是从贵族的棺椁中发现, 就像卫斯理电影中的金缕玉衣。 他站在百年战争的对立面, 或者是要上演新的双城记。 他需要一杯左岸的红酒, 甜度必须是解百纳和赤霞珠中间值。 它不能潜游在著名的酒庄, 被长久封存在湖底的橡木桶, 那名讳是贵族圈骄傲的通行证。 他嘴角的雪茄咀嚼着卷舌音, 在《我的名字叫伊莲》的音乐中流淌。 黑胶唱片并没有走火, 不能将一只误入的壁虎杀死。 在他的浙大单人宿舍没有盘头的女仆, 或者你可以理解他是落魄的贵族, 来不及将家族的荣耀一起移民到东土。 他甚至将鹅毛笔都丢弃在书桌上, 只有一张法语选修课的信纸, 上面留存着柳树般的字母书写体, 落款的名字是他今后生活的星系总和, 包含着复仇、决斗和丢失的庄园: 请叫我让·皮埃尔男爵。 邻居的遗产 在一座巨型城市, 这一次的走失是永恒的走散。 当房契传递他们和我永不相见, 成为我生命中事实性的死者。 可他们会留下点遗产, 比如天台上的种植盒, 那些被圈养的植株, 那曾被他们无限爱抚的瞬间, 就被遗弃在了此地。 而我收养了它们。 就如同云镜将收养我的影子, 浇水的影子、剪枝叶的影子、 将虫卵捏碎的影子。 这些沉重的遗产, 一定会出现在他们某个人的梦中。 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们会重新走进这里, 回味他们曾有过的瞬间。 就像某年的盛夏, 我潜回江南小镇的旧居。 只有那倾斜的斜阳未曾改变, 爬山虎已无法辨认我的面孔, 我后悔没有留下那盆多肉。 电影镜头 我不信任那些电影: 镜头里只有北上广的浮华, 电影里的人也有哀愁, 而这哀愁只是繁荣后的落寞。 他们的摄影机甚至忘记了小巷, 忘记了:这些城市也有不为人知的角落。 我要如何去看待这些情节, 仿佛我们只剩下那点可怜的男欢女爱: 一杯红酒,一个落地窗, 一种为爱等待十年的决心。 我多想看看那些真实的哀愁, 比如绿皮火车里拥堵的人。 比如那些脸色浮肿的留守儿童, 望着窗外的春风, 终于用耳膜捕捉到父母回家的脚步。 在爱情中,理想渐次坍塌: 生活的预制板遭遇着拜金主义的飓风。 我们生活在一部真实的电影中, 如果你此刻没有从角色中觉醒。 它的开放式结局中, 你一定会拥有最坏的那一个。 甚至,在过程的推进和演化中, 你所能拥有的只有哀愁, 剪除了沉溺在哀愁中的那点凄美。 天真的命名 我抽取了蛋糕上的奶油, 留下了那颗瞩目的樱桃。 好像永远杜绝标准答案, 无人说出取舍的秘密。 在阡陌和街道有何区别? 脚步的探测器围绕着计量单位。 当我厌倦于这样的游戏, 就设定在下一个路口的相遇。 那从心理暗示中逃脱的星云, 笼罩着回家后无人的旷野。 在操场上丢弃的皮球, 球衣的汗渍已进入滚筒之中。 那里,回收进球后的喜悦, 几分钟内一切消弭。 梦乡收留站已被塞满, 那奋力奔跑的姿态在瓦解。 我想起多年前的一场长跑。 粗劣的奖杯在第二天开始褪色。 当这些执拗开始被我忽略, 关于天真的命名开始浮现, 在这些细节里我在仰泳, 对着天空永恒的、容易消退的蔚蓝。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4006677657.com/lzzp/lzzp/15946.html |
当前位置: 荔枝_荔枝食品_荔枝营养 >赵俊年自选诗七
时间:2021-7-1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年崇明区教育系统第二届ldqu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